
程美東:協商民主具有世界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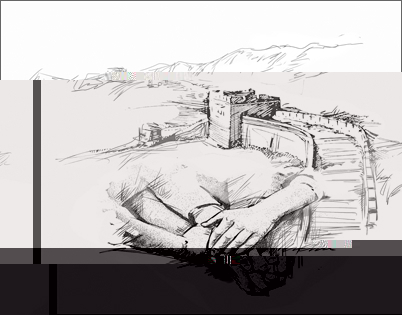
觀點提示
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符合人類共同的精神追求和世界進步的趨勢,更符合人類邁向共産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要使協商民主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實踐中既能充分體現民主本質,又能充分體現中國特色,就必須對協商民主的内涵、特色、意義有更深刻全面的了解。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指出,要“完善人民政協專門協商機構制度”,“堅持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獨特優勢,統籌推進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人民團體協商、基層協商以及社會組織協商,構建程序合理、環節完整的協商民主體系”。《決定》對協商民主在黨領導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過程中的作用做了充分的肯定,對于協商民主總體的實踐内容和發展方向也作了明确的要求。要使協商民主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實踐中既能充分體現民主本質,又能充分體現中國特色,就必須對協商民主的内涵、特色、意義有更深刻全面的了解。
協商民主充分體現了民主的本質内涵
作為現代政治意義上的民主(democracy),是從日文轉譯過來的外來詞。其本義是多數人的統治。這個意義上的民主,中國的詞彙雖然沒有,但不等于中國人不講究民主。從“多數人的統治”這個意義上來看,中國人很早就有民主的價值訴求和具體的實踐形式,這集中體現在中國人政治生活傳統中所一直奉行的“民意”原則。所謂“民意”原則,就是中國人無論對于政治人物的選取,還是對于政治和決策的評價,不是靠一人一票的精确統計來确定,而是以一定的社會道德和政治道德為标準、以口耳相傳為主要途徑而形成的“民意”為基礎來加以衡量。“民意”雖然不像選票那樣直接、精确,但是從價值訴求的角度來看,它與票決制選舉的精神是一緻的,那就是要符合多數人的意願。而且,我們這種“民意”所包含的“民”比“選民”更要廣泛,社會上所有可以表達自己意願的人都包括在内,不受年齡、性别、族别、區域、身份等限制。所以,雖然這種“民意”表達有點模糊,有時候也會受到權力、輿論、道德等因素影響,但總體上看,在很早就廣土衆民的古代中國,通過“民意”的方式來影響政治生活無疑是當時社會條件下很成功的辦法。正因為我們有悠久的“民意”政治文化傳統,所以,當清末民初“democracy”作為政治詞彙傳入中國時,我們很難用漢語表達,連精通日語的李大钊先生都沒有簡單地移植日語的“民主”一詞,有段時間他甚至用“民彜”來表達其政治理想。他1916年曾寫過《民彜與政治》一文,認為“民彜者,可以創造曆史,而曆史者,不可以束縛民彜”。大钊先生這篇文章裡對于“民彜”作了三個方面的定義,“首訓器,次訓常,後訓法”。這裡的“器”指古代中國用于祭祀的器具,乃當時最為神聖的象征,可以說就是指代民心;“常”,此處指的是常道、常理,就是人的本性,這也是一種民心的表示;“法”,在此處就是指體現出衆民意志的法律。總體上看,李大钊所講的“民彜”其實就含有民意、符合衆民願望的意思。大钊先生之所以不用“民主”這個革命黨人早已熟知的詞語,恐怕與他對于“democracy”一詞所具有的複雜性理解有關。
今天我們一般人對“democracy”一詞所對應的“民主“的理解,主要還限于選舉性民主、競争性民主層面。而選舉性民主太過于強調形式上公平,卻不一定能夠保證結果的正義。例如按照絕對票決原則選舉出來的領導人不一定是德才兼備的,票決選舉通過的一些決策也不一定符合多數人的長遠利益。協商民主就是要超越選舉性民主、競争性民主的缺點,一方面要充分體現人民的意願、利益,另一方面又不能簡單地受制于票數。
關于如何實現協商民主,《決定》提出“豐富有事好商量、衆人的事情由衆人商量的制度化實踐”。就是說,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通過協商找到全社會意願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這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協商民主是符合中國政治文化的民主形式
為何在中國要搞協商民主?這與中國的政治文化傳統有很大關系。雖然古代中國就特别強調政治統治要順應民意、體現民意,但由于很早就形成了龐大的社會和國家,古羅馬、古希臘那樣的公民一人一票直選式民主在中國無法實施。錢穆先生就此曾經有過分析:“中國的立國體制和西方曆史上的希臘、羅馬不同。他們國土小,人口寡。如希臘,在一個小小半島上,已包有一百幾十個國。他們所謂的“國”,僅是一個城市。每一城市的人口,也不過幾萬。他們的領袖,自可由市民選舉。隻要城市居民集合到一曠場上,那裡便可表見所謂人民的公意。羅馬開始,也隻是一城市……中國到秦漢時代,國家疆土,早和現在差不多……何況中國又是一個農業國,幾千萬個農村,散布全國;我們要責望當時的中國人,早就來推行近代的所謂民選制度,這是不是可能呢?”
中國古代國家那樣的疆域廣闊、人口衆多、地形複雜,怎麼實現有效管理?靠投票不可能,開全國大會更不可能,日常國家治理主要是通過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精英群體來實現,遇到複雜的問題則可以通過各個層面代表人物的溝通協商來通達民情民意,最終達到相對平衡的共識。中國古代社會縣級政權以下長期實行的鄉紳治理格局,某種程度上就是一種協商治理模式。中國傳統社會重血緣家族關系,重人情、講倫理,重秩序、重和諧,這些社會取向使得中國人習慣于用協商的辦法,通過互相禮讓、互相理解來解決問題,而不是用冷冰冰、硬邦邦的投票來處理血緣深厚的社會關系。協商民主非常吻合更看重結果正義的中國傳統文化習俗。
協商民主也是近現代中國政治的重要經驗。辛亥革命後,中國一些資産階級政治家曾經搞過選舉民主和競争性民主,結果陷入長期的混亂,國将不國。中國共産黨從抗戰時期開始,就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實行協商民主。在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共産黨專門召開全國政治協商會議,而後在全國實行推廣協商民主的辦法。今天中國的政治發展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生動活潑又富有效率,這與協商民主有密切關系。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70餘年,就是協商民主開展的70餘年,已經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協商制度體系。從協商主體的區分來看,協商民主呈現出廣泛、多層次、制度化的特點,形成了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人民團體協商、基層協商及社會組織協商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其中人民政協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安排,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專門協商機構。從協商涉及的範圍來看,有全國性的、有地方性的、還有部門性的。凡是涉及全國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體人民和全社會廣泛商量;涉及一個地方人民群衆利益的事情,要在這個地方人民群衆中廣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衆利益、特定群衆利益的事情,要在這部分群衆中廣泛商量;涉及基層群衆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層群衆中廣泛商量。
總之,凡是涉及人民利益的事情,中國共産黨各級組織及其領導下的各級政府都很注重以協商民主的方式來解決。社會主義中國,必須要堅持黨的領導,也必須要堅持依法治國,但更要發揚人民民主。在中國這樣國情特殊的國家,發揚人民民主的一個重要渠道就是要運用好協商民主的方式,遇事多商量。
協商民主是中國對人類政治文明的獨特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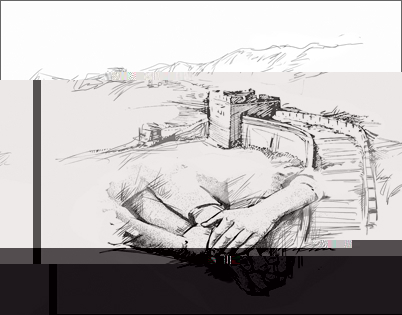
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符合人類共同的精神追求和世界進步的趨勢,更符合人類邁向共産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民主是廣大人民群衆在同剝削階級、壓迫階級漫長鬥争史上的經驗總結,也是勞動人民長期的奮鬥目标,是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重要内容。馬克思、恩格斯等無産階級革命導師創立共産主義理論,指引世界無産階級同資産階級作鬥争的重要思想武器就是民主。正是為了實現無産階級民主、實現勞動人民的徹底解放,全世界無産階級才滿腔熱情、義無反顧地投入反對資本主義、反對資産階級的波瀾壯闊的共産主義運動,極大地推動了人類的進步曆程。所以,毛澤東同志畢生都把人民民主視為共産黨人的神聖使命;所以,鄧小平同志反複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所以,習近平總書記堅定宣示,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協商民主就是社會主義民主的具體實現形式,是社會主義民主在中國的具體化。
協商民主鮮明地體現了中國特色。它深深紮根中國文化,立足中國實際,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這是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通過協商民主,我們既做到了充分發揚人民民主,讓人民行使了當家作主的權利,又避免了簡單競争民主和選舉民主的負面影響,對于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理想的秩序、效率、幸福的奮鬥目标的實現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充分體現了中國人的政治智慧和人文情懷。
協商民主不僅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創舉,對于人類政治文明也是重要貢獻。現在世界上一些和中國有相似國情的國家,長期照抄照搬西方選舉民主、競争民主,卻沒有取得與西方發達國家一樣的社會發展效果,有的反而長期貧困、落後、混亂。以協商民主為重要内容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無疑給這些國家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參考和資鑒,提供了中國智慧和方案。就這一點來看,協商民主具有世界意義。
(作者程美東,系beat365官方网站教授、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發展研究基地負責人兼首席專家)
《中國教育報》2020年4月23日 第5版 理論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