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中共黨史要講究閱讀方法,做到手腦并用。動手讀書,主要包括批注法、摘錄法和劄記法3種方法。用腦讀書,主要包括鈎玄提要、細心揣摩和學而時習3種方法。手腦并用既有利于訓練思維,養成一種獨立思考的習慣,也有利于訓練技能,養成一種獨立寫作的習慣。更為重要的是,它還可以收到“學以治之”“思以精之”“友以磨之”的功效,這是我們學習中共黨史的一種理想狀态。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了“務求實效”的學習目标和要求,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學風,凸顯了善讀善學善思在黨史學習中的重要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曾經對如何讀書進行過深入讨論,他指出:“一方面,讀書要用‘巧力’,讀得巧,讀得實,讀得深,懂得取舍,注重思考,不做書呆子,不讓有害信息填充我們的頭腦;另一方面,也不能把讀書看得太容易,不求甚解,囫囵吞棗,抓不住實質,把握不住精髓。”
就中共黨史的學習而言,關鍵是要做到手腦并用,并在此基礎上實現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的目标。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習近平總書記非常重視思考在學習中的作用,把它作為“善讀書”的最重要體現。
這是因為我們的知識,無論是看來的還是聽來的,都隻是零碎的記憶,算不得自己的東西。隻有對它動一番手腳,或做批注,或做摘錄,并按自己的思路整理過,用自己的語言記述過,那樣的知識才算是自己的。
動手讀書是實現善學善思的有效路徑,根據功能不同,具體可分為批注、摘錄、劄記3種方法。
批注法。批注法是一種最為常見的讀書方法,可以幫助人們對抗大腦的遺忘規律。朱熹說:“用力深,便見意味長;意味長,便受用牢固”,講的就是類似的道理。
人們常用做記号和寫批語來作批注,這也就成了批注法常用的兩種形式。對于寫成批語的批注而言,位置不同,稱謂不同。例如,批在書頭上的稱作“眉批”,批在句子間的稱作“夾批”,批在段落旁的稱作“旁批”,批在段落後的稱作“尾批”等。
批注的内容可以分為以下4種:一是“注解”。遇到難以理解的字詞或概念,在弄清後,記在書的空白處。二是“綱要”。用概括性的語言,将文章的主旨要義寫在書的空白處,方便把握文章脈絡,在重新閱讀時,做到一目了然。三是“評論”。将讀書時産生的各種感想、見解或疑問随手記在書的空白處。如若不然,過後這些寶貴的思想火花就會蹤迹不見,再難追尋。四是“警語”。對于發現的重要段落或主要論點着重标記出來,為日後重點閱讀提供抓手。
在黨史人物中,毛澤東所留下的批注在數量上可以說是相當驚人的。單是豐澤園的圖書室裡,就有13000多冊圖書被他批注過。至于在其他書籍上,毛澤東寫過的批注就更加難以計算了。
一本《倫理學原理》,全書不過10萬字,他卻用工整的小楷在書的空白處寫下了12000字的批語。一部《二十四史》,共3213卷,約4000萬字,他不僅全部研讀過,而且還在許多冊上留下了大量的批注。
據胡繩回憶,20世紀50年代初,毛澤東在與他談到人口問題時,胡繩提到中國最早主張控制人口的是清朝乾隆年間一個叫洪亮吉的人,他比馬爾薩斯還要早。毛澤東對此很感興趣,要胡繩把洪亮吉的文章找來看。胡繩向圖書館借了一套《洪北江文集》送去。
毛澤東讀後,不僅在“有些文句旁邊加了圈點,而且還改正了一個印錯的字。本來是看談人口的文章,毛主席連帶将洪亮吉的傳也看了”。後來,胡繩去舊書店買了一套同樣的書,換下了毛澤東批注過的那一套,歸還給了北京圖書館。
摘錄法。人們常說,買書不如借書,借書不如抄書,抄書不如摘錄。摘錄法是一種深度閱讀的方式。朱熹說:“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将來甚處用得”,就有這樣一層考慮。
因此在學習黨史的過程中,可以在讀完一本書後,馬上把一些表述摘錄下來,并在摘句之下,注明原書的書名、篇章、頁碼、出版時間等,以備應用時查考。這種摘抄工作實際上是讀書的一種笨工夫,但是有學者卻說,他讀一生的書,隻在這種最笨的工作中,“才得到一點受用”。
當前,互聯網技術為材料的查找工作帶來諸多方便,然而即便如此,也不能替代摘錄工作這個笨工夫。這是因為在大數據時代,一些虛假信息和錯誤知識,也常常會像細菌或病毒一樣,從四面八方侵襲過來,需要引起我們高度警惕。
劄記法。劄記也叫随筆,它是在讀書過程中,把自己的收獲、感想、意見、質疑、評價和啟發等,記錄下來的一種筆記形式。
寫劄記,不僅要有明确的問題意識,還要經過一番深入的思考,如若不然,像個思想懶漢,即便天天有筆記,也不會有心得;即便天天有問題,也不會有答案。那樣的人隻是“文抄公”,那樣的筆記隻是“流水賬”,嚴格說來,不能叫讀書劄記。這也不是我們學習黨史的目的所在。
劄記法還有兩大益處:一是訓練思維能力,養成一種獨立思考的習慣。長此以往,自然就形成了一種判斷力,再讀書時就不會是人雲亦雲。二是訓練寫作能力。長此以往,自然就形成了一種創作力,再寫作時就不會是下筆凝滞了。有了這兩種能力,對于一門學問,我們就不用再擔心缺乏駕馭運用它的才幹了。
讀書是個精細活,所以要手腦并用,前文講動手讀書,未嘗不用大腦,現在講用腦讀書,也未嘗不動手腳,隻是各有側重罷了。不過相對于動手來說,用腦的利害關系更大。
魯迅說:“讀死書會變成書呆子,甚至于成為書廚”;“讀死書是害己,一開口就害人”。現在看來,之所以會“讀死書”,之所以會成為“書呆子”,都是讀書沒用腦的緣故,其結果自然是害人害己。下面談一點用腦讀書的方法。
鈎玄提要。韓愈在《進學解》中說:“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玄。”也就是說,讀書要“獨觀大意”“采其精英”,不要隻拘泥于字義,這是用腦讀書的第一要義。讀易書如此,讀難書也不例外。
當然,讀書要真正做到鈎玄提要,也絕非如此簡單。朱熹說:“先一書費許多工夫,後則無許多矣。始初一書費十分工夫,後一書費八九分,後則費六七分,又後則費四五分矣。”
也就是說,從知道鈎玄提要到做到鈎玄提要,中間還需要通過大量的閱讀實踐,當下可以先從下面兩個關鍵環節入手,進行嘗試。
關注“序例”。這主要包括書的序言、凡例和後記。一般人讀書有個壞習慣,以為讀正文就行了,“序例”可以不看,這其實是個誤區。
序言一般會講明寫書的綱領、目的。凡例是提示讀者應該注意的地方。後記也叫題跋,在這裡作者一般會交代寫作經過,有時還會提出一些問題,引發讀者思考。這都是我們把握全書要旨的關鍵所在。
除此之外,從一本書的“序例”裡,還會得到一些額外的收獲。比如,胡喬木在《中國共産黨的七十年》一書的題記中,就提出書寫黨史應遵守這樣一個原則:“既實事求是地講出曆史的本然,又實事求是地講出曆史的所以然。”
又比如,張靜如在《唯物史觀與中共黨史學》一書的緒論中指出,黨史研究中有三大頑疾:“淺、窄、粗。淺者,研究中叙述多,分析少,理論性弱;窄者,研究領域狹小,重複研究多,創新研究少;粗者,分析不細緻,用材不講究。”這都是我們從正文中看不到的真知灼見。
關注“書眼”。所謂“書眼”就是全書的核心與精華所在,抓住“書眼”就能極大地提高閱讀效率。這裡面有兩個要領:一方面是要讀好“大字”,即認真閱讀書的目錄。這樣可直接抓住它的綱要,使全書若網在綱,其重點一目了然。另一方面還要會看“小字”,因為“小字”中也常有大信息。
錢穆早年讀《水浒傳》,先生對他說:“汝讀此書,隻讀正文大字,不曾讀小字”;“不讀小字,等如未讀,汝歸試再讀之。”錢穆聞聽此言,“大羞慚而退。歸而讀《水浒》中小字,乃始知有金聖歎之批注”。
事實上,讀《水浒傳》,不讀金聖歎的“小字”,讀《紅樓夢》,不讀脂硯齋的“小字”,就不能抓住它的“書眼”。
當然,對待“書眼”,也須因人而異,不可一概而論。對于已知的知識,即便它是書的重點,我們也可以視而不見;而對于未知的知識,且又是書的關鍵,我們則必須盡全力将之“拿下”。
細心揣摩。朱熹說:“為學讀書,須是耐煩細意去理會,切不可粗心。”講的就是細心揣摩的意思,這也是用腦讀書的一大關鍵。
具體就是指我們在讀書時,不要讓問題在眼前一閃而過,而是要讓它在頭腦裡反複發酵,最後變成自己的知識。否則,讀書不但不長“精神”,反而隻生“癡瘤”就不好了。當然,這是就一般道理來說的,具體到黨史的學習研究,就要在“揣摩”上做文章。
揣摩作文的“章法”。古人寫文章講究“鳳頭、豬肚、豹尾”。“鳳頭”就是說文章的開頭,要精緻凝練,且富有懸念;“豬肚”是說文章的主體部分,要内容充實,給人豐滿的印象;“豹尾”是說文章的結尾,要沉穩有力,不應當拖泥帶水。
梁啟超說:“讀一書,專取一個注意點;讀第二遍,另換一個注意點。這是最粗的方法,其實亦是最好的方法。幾遍之後,就可以同時有幾個注意點,而且毫不吃力。”對于這個“最好的方法”,我們當然要學習和借鑒。
揣摩書中的“義理”。這是讀書最難的部分。章學誠說:“理之初見,毋論智愚與賢不肖,不甚遠也。再思之,則恍惚而不可恃矣。三思之,則眩惑而若奪之矣。”
也就是說,對于書中的道理,“初見”“再思”“三思”皆不可得,有時甚至還會頭昏腦漲,産生失去自我的感受。我們隻有越過這個階段以後,才能到達至高的境界。須知讀書的時候,之所以會感到“恍惚”“眩惑”,那是讀者從“義理”的外邊進入到它的内部,身心随着它的變化而變化的結果。這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段,千萬不可因此中途而廢。
其實,在黨史學習中,如果遇到某個問題,感覺讀了許多書,記了許多材料,并且認真揣摩過,但仍然感覺像是一團亂麻,這時就半途而廢了,着實是一件可惜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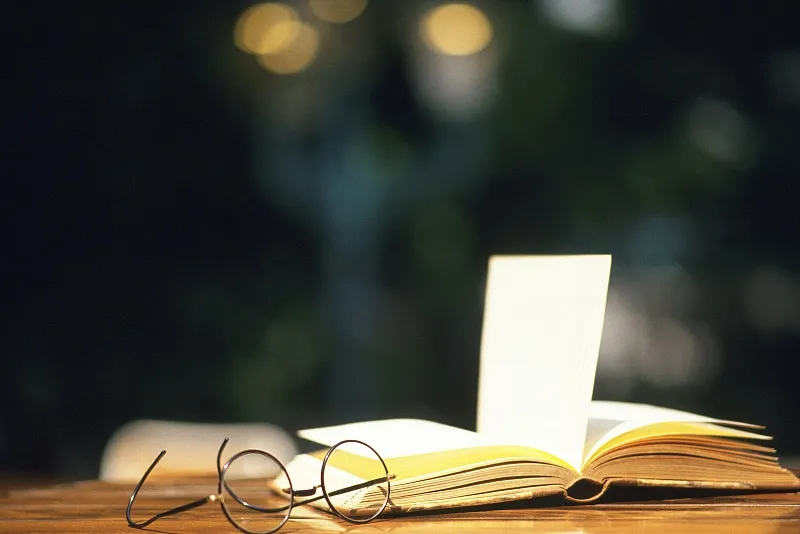
學而時習。這是孔子的讀書方法,他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不過對于這個“習”,大家有不同的理解,有的說是“溫習”,有的說是“實習”,但無論哪一種說法,都是要換個腦筋讀書的意思。
所謂“溫習”,即把讀過的書再讀一遍。因為一般人讀書,隻知道“瞻前”,不知道“顧後”,所以知識難得長久。因此,我們讀書的時候,要一面去“溫故”,一面來“知新”。孔子說:“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這是讀書的一種理想狀态。
在黨史學習中,“故”是實在的事實,“新”是人們的認識。人們對于實在事實的認識,終不能完全,所以要不斷地“溫故”,由此不斷地産生新的認識,如此循環往複,我們便可日益接近曆史的真相了。
李大钊說:“曆史是有生命的,僵死沈[陳]腐的記錄不能表現那活潑潑的生命,全靠我們後人有新的曆史觀念,去整理他,認識他。”由此可見,運用新的史觀,重讀舊的記錄,做好“溫習”這件事,也是黨史學習學出成效的好路徑。
所謂“實習”,即把學到的知識再檢測一遍。古人說:“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毛澤東早年就很重視這一點,正如他在緻湘生信中寫道:“吾于課程荒甚。從前拿錯主意,為學無頭序,而于學堂科學,尤厭其繁碎。今聞于師友,且齒已長,而識稍進。”
讀書中,有不懂的也不大願去請教人,生怕問了人家丢面子、現了醜,這實在是要不得的。《書經》上說:“好問則裕。”《禮經》上說:“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這些都是可以作為我們讀書座右銘的。
所以,關于讀書的方法,前面講“學以治之”,然後講“思以精之”,現在又講“友以磨之”,這樣才算把它講全了。
作者:周良書,beat365官方网站教授、博士生導師
文章來源:《前線》雜志2021年第5期,原标題“中國共産黨曆史的閱讀方法”

